
︱私房歌話 #1︱那些年,讓我汲取音樂養分的雜誌
- posted April 5, 2021
為了寫這篇文章,我翻箱倒櫃地從房間各個角落找出所有印象中買過的音樂雜誌,趁機拍照整理一番,然後翻著翻著就翻出了神,各種回憶不斷倒帶。
我記得第一本引起我興趣深入閱讀的音樂雜誌是 Melody Maker,這一份號稱英國最早出版的音樂週報當時並沒有在本地出售,我是在中學時期上 British Council 圖書館時,好友介紹給我閱讀的。首次接觸就有很大的挫折感,因為裡面介紹的樂隊名字我幾乎都沒有聽過,看了他們年底選出的30張年度最佳專輯的名單,十之八九連封面都沒有見過,直叫我這個西洋樂迷感到汗顏,那是1987年的事情了。因為不服氣,我每期都借回家裡看個夠,誓要搞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,為何連我當時鍾愛的 U2 樂隊也被他們不屑一顧。 80年代沒有互聯網,所有音樂資訊都是從電台、電視台、錄影帶、報章、雜誌和唱片行獲取,我花了將近半年時間才了解雜誌內最常出現的字眼 Indie 是什麼意思,不是印地安人,不是 Indiana Jones,那個 Indie Chart 就是非主流市場的排行榜,難怪只聽 Billboard Top 40 的我會一無所知。
知恥近乎勇,我靠這本雜誌惡補非主流音樂的資訊,記下受訪樂隊的名字,然後在本地唱片行的架子上耐心地搜索,偶爾看到一兩盒卡帶就買下來先聽為快。那時候找到 REM、Sonic Youth、Jesus and the Mary Chain、Nick Cave and the Bad Seeds、The Waterboys、The House of Love、The Wonder Stuff、All About Eve、Green on Red、Talk Talk 的專輯都如獲至寶,他們的歌曲都與眾不同,創意十足而且很有力量,就算身邊沒有知音,我還是愛不釋手,因為流行歌曲給不到這種感覺。 Melody Maker 雖然是英國老牌週報,但內容卻十分先鋒,與老氣橫秋的美國雜誌 Rolling Stone 完全不一樣,後者在書店隨手可得,但我卻從來不會購買,只會定期到圖書館借閱 Melody Maker ,直到 British Council 停止訂閱後,我才開始轉向同類型的 NME(New Musical Express),因為我可以向印度書報攤訂購這份週報,雖然一般上會過期六週,但為了繼續汲取音樂養份,我沒有放過這個機會。

八十年代末期,大約從1988年開始,一股 Alternative Music 的風氣突然興起,我因為經過 indie 的洗禮,所以一拍即合,開始投稿給文藝雜誌推介這類音樂。當時還沒有「獨立音樂」這個字眼,我就套用不曉得從哪裡讀來的「另類音樂」作標籤。那位介紹我看 Melody Maker 的好友去了加拿大留學,特地寄回一盒 The Sugarcubes 的卡帶讓我解癮,這是經常出現在 Melody Maker 封面的冰島樂隊,所以我提前認識了樂隊女主音 Björk 那把不可思議的唱腔和演繹方式。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,好雜誌和好朋友對一位音樂發燒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,辦音樂雜誌成了我其中一個夢想,把更多的音樂資訊分享出去。
進入90年代沒多久,1991年 Nirvana 平地一聲雷崛起,Grunge 成了潮流,唱片公司不管原創還是跟風,把類似風格的專輯都貼上 Alternative Music 的標籤來販賣。離開樂隊作個人發展的 Björk 在1993年也一鳴驚人,同一年英國傳媒炮製了 Britpop 這個字眼來對抗美國的 Grunge,霎時間樂壇風起雲湧好不熱鬧。這個時期是我購買音樂雜誌的巔峰,因為除了文藝雜誌,我開始定期替報章寫專欄,大量介紹另類音樂,那些國外進口的音樂雜誌成了我的參考書,相等於我那個年代的「谷歌」和「維基」。除了 NME 和 Melody Maker,我當時在市面上買得到的雜誌包括英國出版的月刊 SELECT、VOX、Q 和周刊 Kerrang!、美國出版的月刊 Alternative Press 和 Spin、托朋友帶回的香港《音樂殖民地》雙周刊、以及只買到兩期的中國《摩登天空》月刊,這就是我每個月的精神糧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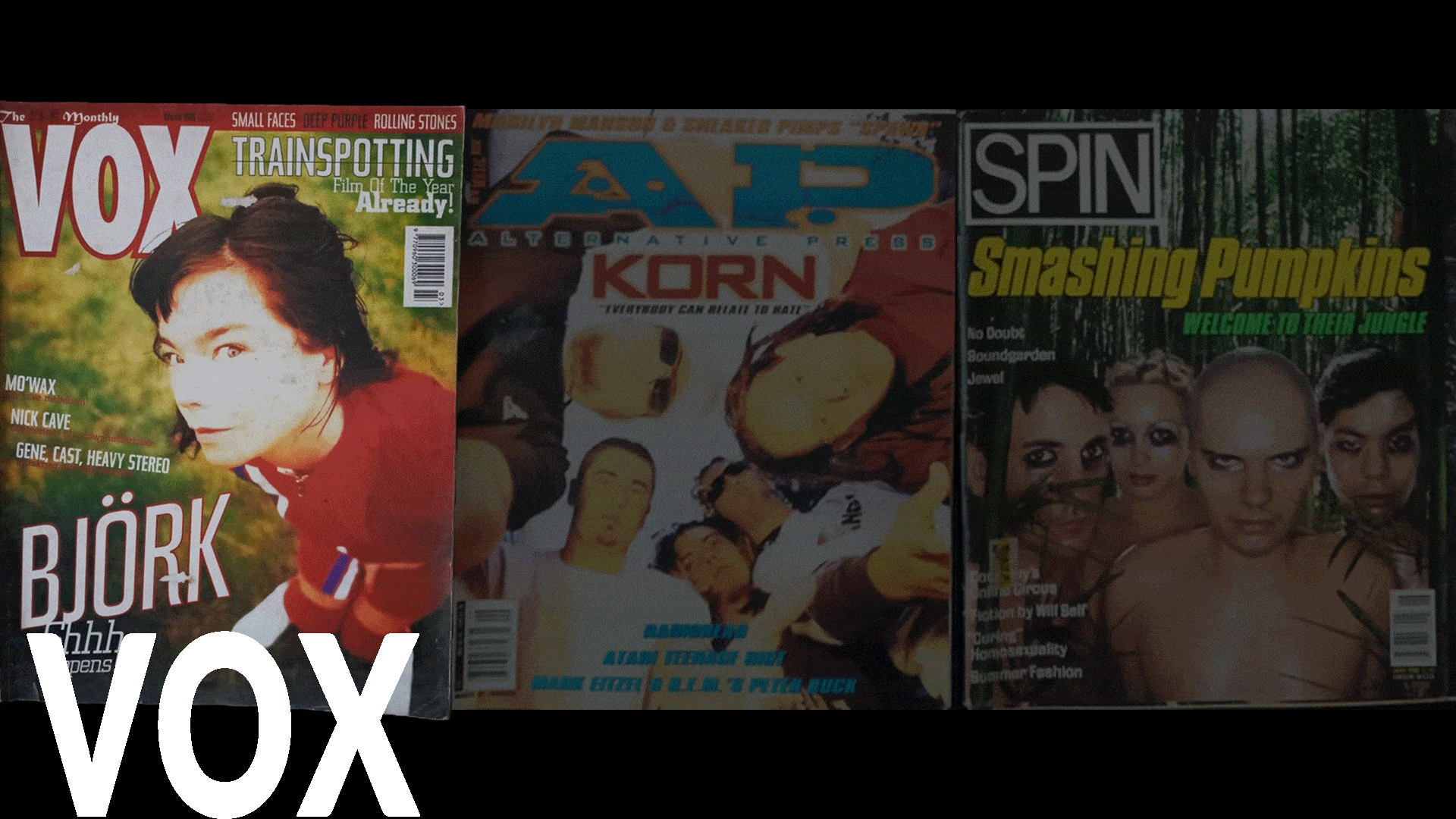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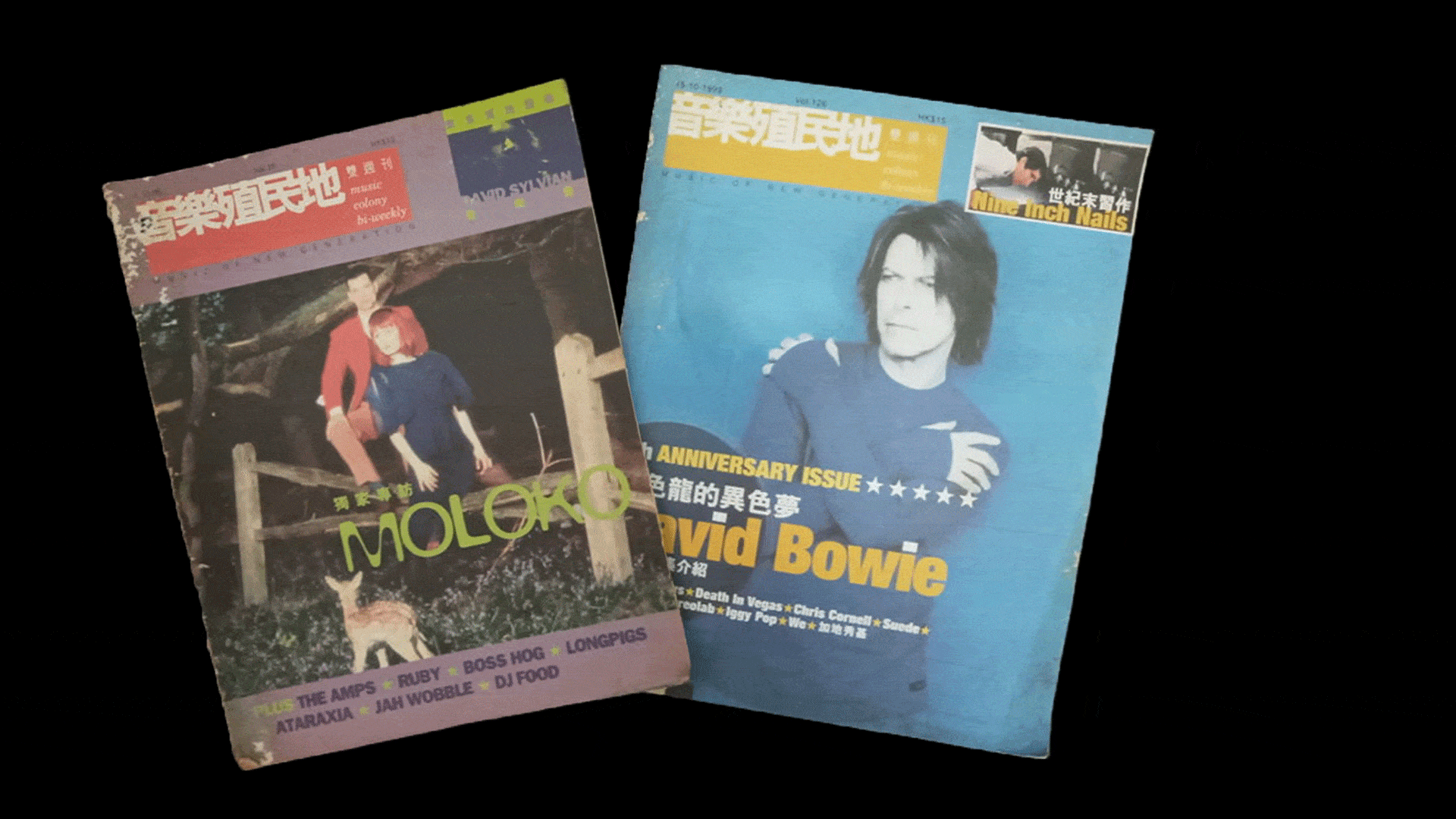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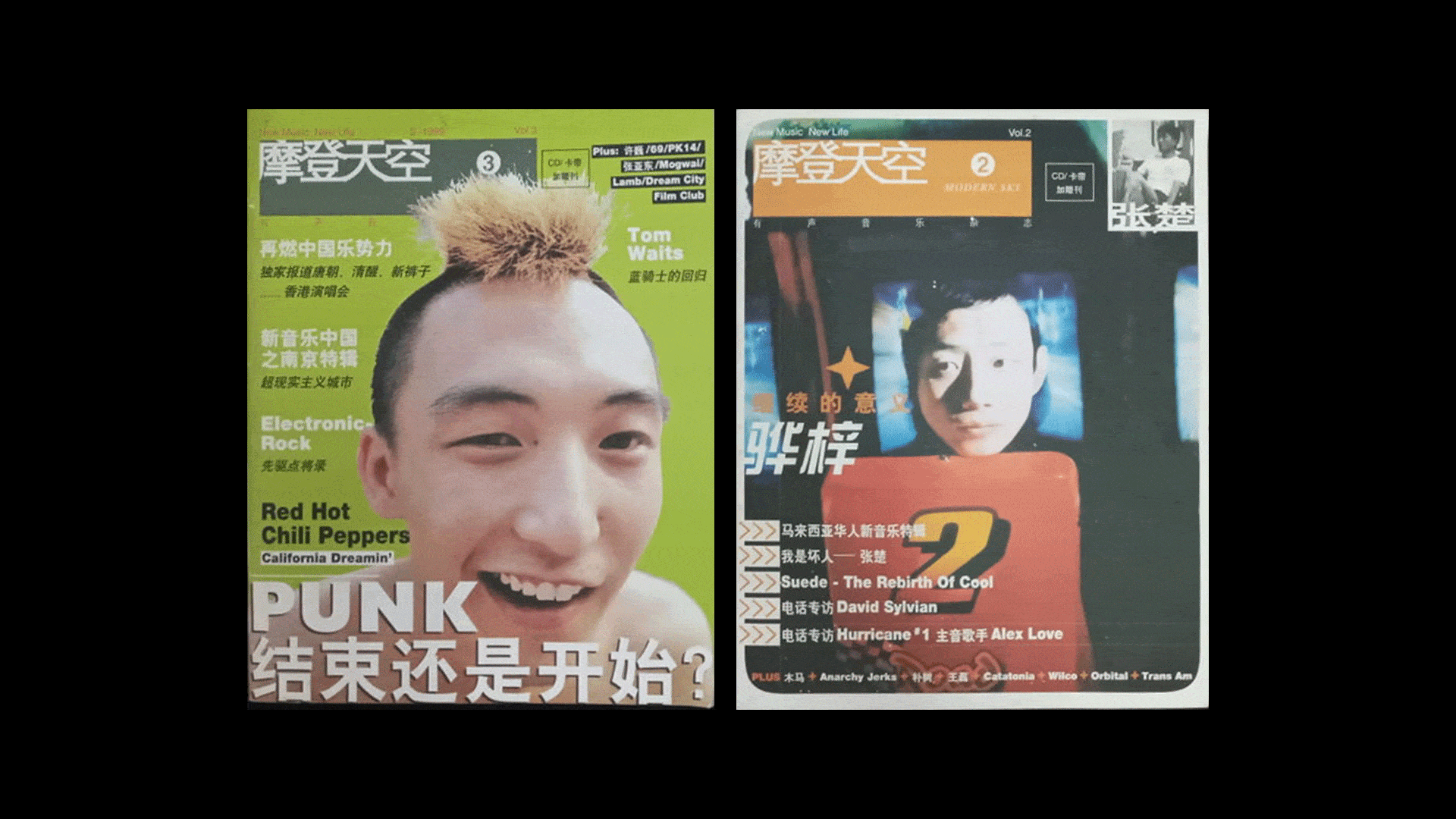
上述提及的眾多雜誌當中,只有 Alternative Press 和 Kerrang! 繼續實體出版至今,其他都已經停刊多時,連創刊34年的 Q 也在2020年敵不過疫情而在7月停止出版,只有 NME 和 Spin 在實體停刊後繼續以線上版發行。這些雜誌當年各有本身的風格和讀者,Alternative Press 早期以報導美國地下音樂為主,介紹主流音樂以外的場景,後期轉向比較重型的 hardcore 樂隊。 Spin 則聚焦校園搖滾和另類音樂身上,主要是提供 Rolling Stone 這類傳統雜誌不會報導的音樂資訊,這兩本雜誌都是認識美國樂隊的入門讀物。 SELECT 則是一本應 Britpop 樂潮而誕生的雜誌,Britpop 這個字眼首先出現在這本雜誌內,有很多樂隊的第一手消息,不過當潮流降溫後,它也隨之消失。 Q 走的是精裝路線,印刷精美內容豐富的月刊,厚厚一本份量十足。 VOX 則是 NME 母公司 IPC Media 用來抗衡 Q 的雜誌,內容比較精緻,可惜銷路欠佳,很快就停刊。 Kerrang! 則是英國出版的重金屬音樂雜誌,很受本地馬來讀者的歡迎。為了平衡專欄內容,我全部都看,並根據雜誌的推薦指南,買了不少不同類型的專輯,實行多看多聽多寫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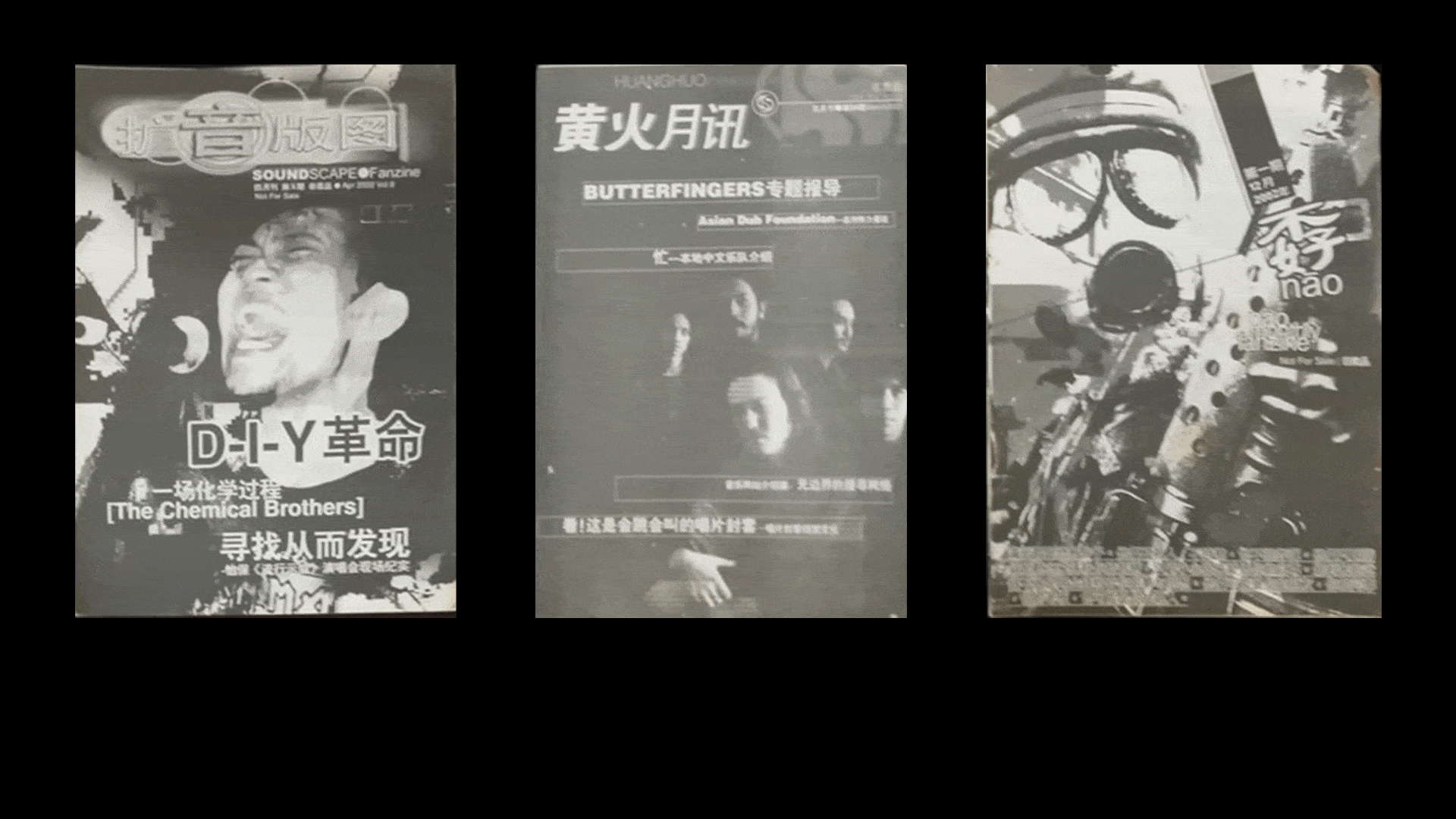

我在1997年與重陽樂隊發起「黃火」運動後,為了讓本地中文樂隊認識更多音樂類型,就在1998年6月推出了《黃火月訊》,一開始幾乎由我自己包辦撰文,其他人負責排版,用複印方式出版,也算是圓了一部分辦雜志的心願。我編了前面三期過後功成身退,交給林悅接手主編,後來改為印刷版本,從不間斷地出版了34期,為本地獨立音樂留下珍貴的文字紀錄。之後擴音版圖和孬樂隊也辦過月訊,但只出了大約十期左右,2003年開始就沒有了下文,因為大家已經化為行動,搞影響力更大的音樂節去了。黃火於2001年停止營運後,我在檳城組織了 Soundmaker 繼續本地樂隊的活動,這個名字其實也是向影響我至深的 Melody Maker 致敬。這個時期我變成小型音樂會(Gig)的搞手,為了對本地樂隊有更多的認知,我開始訂閱多本馬來音樂雜誌,其中有銷量最大的 ROTTW(Rhythms of the Third World),他們還派記者報導過我的音樂會,另一本是與演唱會有關的 Konsert;英文雜誌主要是看 KLue 和 Dragon,因為有不少關於獨立音樂場景的報導。互聯網此時開始普及化,雜誌和報章一樣開始式微,我也減少買雜誌的習慣,如今只要聽到有任何雜誌停刊的消息,我內心都忍不住感嘆。
附錄相關雜誌的命運:
- Melody Maker(1926 Jan – 2000 Dec)
- NME(1952 Mar – 2018 Mar,改為線上版)
- Kerrang! (1981 June至今)
- Spin(1985 – 2012 Sep / Oct,改為線上版)
- Alternative Press (1985 June至今)
- Q (1986 Oct – 2020 July)
- SELECT(1990 July – 2001 Jan)
- VOX(1990 Oct – 1998 June)
- 音樂殖民地(1994 Oct – 2004 Oct)
- 摩登天空( 1999 May – 2000 Nov)

陳偉光
馬來西亞資深劇場人,影痴與音樂發燒友,先後創辦《剃刀實驗劇場》和《戲劇家族》,發起《黃火》推廣中文樂隊演出,經營檳城地下音樂基地 Soundmaker。曾任職檳城光明日報副刊主任,先後在光華日報、光明日報、星洲日報耕耘藝文專欄。近年從劇場教學退休後,喜歡在社交媒體撰寫各類藝評。
